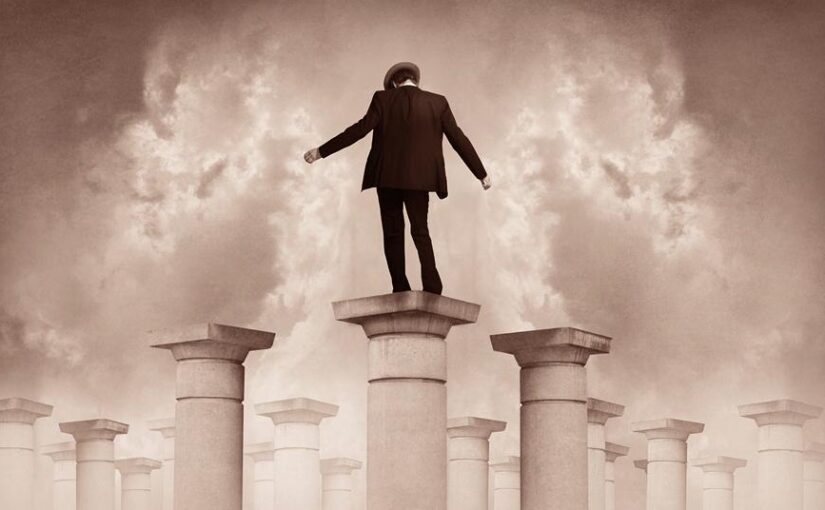译者:Tiffany Liu
每当那些海龟宝宝孵化之时,他们所面临的都是既凶险又充满未知的旅途。那些在掠夺海龟宝宝性命的企图扰乱钓线的海鸥也是他们的威胁。
海龟们悄无声息的来自海洋,当她们浮出海面时,她们的壳峰先浮出海面沐浴月光,紧接着是她们的头还有身子。抛开她几千公里的旅程,她把自己拉上岸,在岸上找到一个平静的沙丘,挖一个沙坑,把她几百个海龟蛋下在里面。然后,闪着受过磨练的双眼,她转了一个弯,沿着沙滩顺风而行,而后进入了梦乡。
在弗罗里达的亚特兰大海湾中心的Archie Carr National Wildlife Refuge,同样的场景每天会上演许多遍。今年,六七月份的时候,约2万5千只海龟在Refuge的海滩上筑巢。夏天过后,这些巢穴将会变得非常拥挤,因为这些巢穴离得太近了,以至于他们留给彼此的空间太少。
这个保护海龟的机构成立于1982年。许多年过后,在这些有着细长形状,长度约有两个国家长的岛屿上被迫建立了宾馆和公寓大楼。在一些地方,Refuge不再覆盖那些介于沙丘和海洋之间的带状岛屿。少数的高层建筑陡然耸立,但大部分地区的建筑仍是一家一户的海滨房。稀疏的人口减少了晚间的灯光,这对海龟们是非常有利的。海龟在天黑以后产下蛋并且试图躲避那些被灯光照射的海滩。大约两个月过后,这些蛋孵化出来,这些新出生的海龟宝宝会被那些灯光吸走注意力,但他们所奔向的地方不是大海,而是街道。当地管理人规定岛上的住户不要在晚间开灯,尤其禁止白色灯光出现在夜晚的沙滩上。“海龟可以在海滩上与人类共存,但它们需要的是黑暗并且安静。” Refuge的执行助理Anibal Vazquez说道:“这是我们目前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了。”
在Refuge成立的这三十多年中,工作人员们完成了许多了不起的工作,包括保护海龟,甚至帮助那些濒危灭绝的海龟增产。这些海龟中最常见的是蠵龟,约有3英尺长300磅重。在八月中旬,约有1万3千多只蠵龟在这里筑巢。这个种类的海龟被美国认为是濒危灭绝的品种,但在Archie Carr National Wildlife Refuge,蠵龟的数量一直很稳定。最好的一年是2012年,约有1万8千只蠵龟驻扎在这里繁衍。
但最成功的故事是关于绿海龟。1982年Refuge成立之时,只有下100个绿海龟的巢穴在弗罗里达被发现。(科学家认为巢穴数量之所以这么少,可能是因为绿海龟被其他物种所捕食,因为他们的肉很美味。)但是,自从Refuge还有当地政府严格禁止晚间在沙滩的灯光使用后,绿海龟的数量有明显的回升——虽然上升过程慢但数量却惊人。在2013年,1万2千只动物在这里筑巢,这个数量比去年同期的数量要翻了一番。今年,11,347只绿海龟在Refuge在这里产下了他们的蛋。这些绿海龟还要在这里驻扎两周,也许会打破之前的纪录。“这里(Refuge)原本是蠵龟的大本营,但现在已经被绿海龟占领了”Vazquez说道。
Archie Carr National Wildlife Refuge同时也欢迎其他的海龟,比如58只在今年来到Refuge的棱皮龟。棱皮龟以他们柔弱的壳还有比现今所有海龟都要庞大的身躯而著名。雌棱皮龟和雄棱皮龟最长都能长到6英尺长1500磅重,这个重量相当于一台小汽车。最近我和我的朋友有幸亲眼看到一只在Refuge的棱皮龟。我们在她刚刚筑好的大巢穴中找到了这只巨大的正在产卵的棱皮龟。
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晚上,我们前往坐落于Refuge中心的类似于教室或者海龟博物馆的Barrier Island Education Center。我们像小组讨论一样围坐在一起,讨论海龟的迁徙路线,产卵分布还有海龟种群的健康状态。就当我们的讲师传授知识时,巡逻的工作人员会帮助在岸上的海龟保持他们原本的路线。大约90分钟,巡逻的人员们就发现了一只要上岸的海龟。这些怀孕的乌龟总是喜怒无常,尤其是对人类。这些怀孕的海龟会按“错误”的路线爬行,他们上岸然后再回到海里,只为了恐吓人类。在白天的时候,你可以跟随这些怀孕的海龟观察他们的“错误”爬行。为了保证这些海龟的“错误”路线不会被人打搅,工作人员会跟在怀孕海龟的身后帮她们堆沙丘,挖巢穴还有完成接下来的事情。这时,这些怀孕海龟的激素会是她们昏迷并且麻痹她们产下海龟宝宝。
我们聚集在蠵龟旁。这只名叫Madeleine的海龟正栖息在她的巢中并且把蛋孵在她的蛋室中。她的蛋一个接一个地产下,就像接连不断的乒乓球一样。Madeleine 对于我们的出现显得很紧张(当然,我对于侵犯她的隐私也感到有些怪异)。在最后一个蛋也落地之后,Madeleine 花了几分钟用沙子把所有的蛋都埋好。这简单的的一步也是要格外小心:这些巢穴会被浣熊和其他的捕食者所破坏。做完这些以后,Madeleine 慢吞吞的回到了海中。
如果一切顺利,Madeleine 的蛋会在下个月孵化出来,也许在黄昏之前。孵化出来的海龟宝宝会顶破覆盖着他们的沙子找水喝。每当这些海龟宝宝孵化之时,他们所面临的都是既凶险又充满未知的旅途。那些在掠夺海龟宝宝性命的企图扰乱钓线的海鸥也是他们的威胁。每出生的1千只海龟宝宝中,平均下来只有一只会活到成年。尽管如此,蠵龟仍然坚持不懈的持续着她伟大的产卵工作。也许,在Refuge的帮助下,她的宝宝们能活得更长一些。
By Dexter Filki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