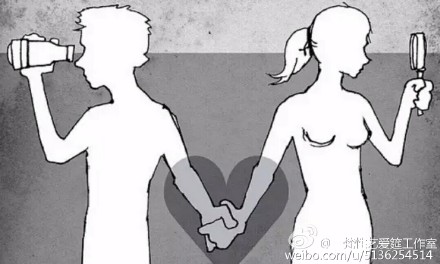译者:Cielo
任何事情都好商量,甚至是一张无法退款的飞机票。
想想当莱恩·杜飞(音)发生了脑外科手术并发症而他不得不取消他自南卡查尔斯顿到拉斯维加斯的飞机票时候发生了什么。
事实上,称其“并发症”还是略显温和了。“我发作了另一场癫痫然后他们发现我右眼前一颗脑瘤的反复。”在南卡查尔斯顿一家饮料分销公司工作的杜飞说,“我必须要进行另一场紧急手术。”
这场癫痫同样使他摔倒,造成了外伤性脑损伤。也就是说:短时间内杜飞将不能飞往拉斯维加斯了。他想知道他的航班是否可以退无法偿还的机票钱。
大多数由飞行常旅客买到的机票都是无法退款的,航空公司声称这使机票的价钱在可以付得起的范围内。如果想要一个更具弹性的情况,你就需要付的更多。但弹性票价更高——非常高——两倍,三倍,有时候甚至是四倍原先不可退还的价格。只有可以报销(机票)的商务旅客会考虑买一张,这也就是这些票原本打算的(服务情况)。
但是如果规则不是用来打破的,就是拿来变通的。航空公司有时候会在他们不退还的这一规则上他们不得不出现特例。比如说,除非你在出发的一周内,那么交通部要求航空公司要么“控制”一桩机票交易24小时要么在一天之内提供全额退款。同样的,航空公司必须在他们取消航班时提供全额退款。
对杜飞来说,这些一个都不适用。他,就像每年成千上万坐飞机的美国人一样,对旅行实在是不太感冒了。旅行保险也许同样无法帮助到他;他的情况可以考虑为“先前存在(preexist)”,这在大多数政策中并没有覆盖到。
他支付的条款同样清晰明了。他可以如计划般乘坐飞机,也可以要求付过差价与变更费$200之后才可赎回的赊欠。这会吞掉他$774元机票的四分之一,不包括差价。
他向美国航空要求退款。答复是:闭嘴。
“我发送了三到四条退款请求,得到的只是自动回复”他说,“在最后一封请求中,我被告知某人可能需要30天来回复。已经60天了,仍然没有人与我联系。”
给他们打电话是不可能的,他补充道。“在这个部门,并没有一个直接的电话号码与专人,而联系到任何人的唯一方法就是发邮件或者传真,”他说。
我询问了美国航空关于杜飞的请求,然后它同意了退还机票款。但它不会说为什么,或者在什么情况下,它可能返还其他无法退款的机票。
“现在就授予豁免和优待的禁令看起来已经是航空体验中不可触碰的规则了,”一位美国航空的执行官说。他说唯一的特例是西南航空,它允许你重新利用钱购买一张机票并且不需要昂贵的费用。
很多年前在美国航空,他说职员们需要很好的得到对顾客说“不”的许可。现在对于“无法退款”规则的特例必须要在“高层”同意。
“所有主要的搬运人们(航空公司)都差不多,唯恐一大部分收入来源被损害,”他补充道。
那么来源到底多大呢?根据交通部,去年大约三十亿美元,相较前年的二十八亿美元些微有所上升。最大的航空公司:美国航空,八亿七千五百万美元。
一份关于我作为消费者拥护者处理的成百上千案子的回顾表示并没有明确的模式来退还无法退款的机票。一个大型线上处理退款要求旅行机构的高级经理说它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消费者默认当一张机票无法退款时是此机构的政策。事实上,这是航空公司的规则,而当机构试图替代消费者申诉时,“很少有好结果”。
一些主要的航空公司严格的秉承着“无豁免,无优待”的原则,只有当乘客去世时才会退还机票款。近亲必须出示死亡证明。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航空公司持有强硬态度,至少不是所有时候。这甚至适用于美国航空。例如,今年的早些时候,莎伦·特里(音)想要退还她美国航空去墨西哥坎昆的机票。她的医生诊断出她患有三阶段的慢性阻塞性肺病与高血压,建议她不要坐飞机。特里收到了一系列的固定回复由某人保证这件事会提交给他“在会计部的同事”。她试图回复这条消息,但她的邮件又被返回来了。
“他们的顾客关系就像不存在的一样,”她说,“我确切地相信他们让消费者几乎不可能得到退款。”
我替她联系了美国航空,它一言不发地退还了她的票款。
美国航空在这件事上并不是全然沉默的。无法退还的机票“一般”无法退款,它在网站上说。“但是,”它补充道,“例外可能会发生在未使用过机票部分的退款。”
他们包括旅客的死亡,或者一个使顾客无法接受的计划变更并造成了旅客旅行超过一个小时的变更。因为任何其他出版规则的缺失,旅客就被丢在那里自己猜测他们的机票是否值得退款。
航空公司如美国航空可能会退还无法退款的机票款——只要你的故事够吸引人。
By Christopher Elliot, Washington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lifestyle/travel/can-i-get-a-refund-on-that-nonrefundable-airline-ticket/2015/08/06/2ac629b8-2ca1-11e5-a250-42bd812efc09_story.html